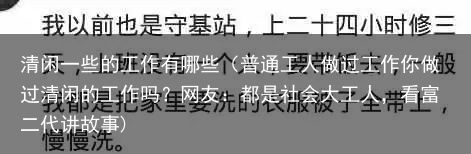当一名工人有啥好处(普通工人的厂庆文章一个普通工人的故事)
舵手已经远去,人们不随他走过的,就失了前行的路。
——题记
太公老家有一座好大好大的,废掉了的工厂。
野花在拉煤车上盛开,机器里伸出绿油油的枝叶,无数充满着生命力的小草顽强的拱破了坚不可摧的水泥地,像地毯一样地从地下钻了出来。
小时候,我常常去那里捉蚂蚱。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抓到一只蝴蝶,或是看见一只田鼠从半米高的杂草堆中一下子猛地窜过去。
有时晚上我睡不着觉,于是悄悄爬起来,摸上一瓶花露水,就跑到工厂里,陪着蚊子与萤火虫数星星。
在北方,能见到整条银河带的地方并不算少。
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就是专属于我与我的萤火虫们的小世界。
这个小世界的名字叫做夏天。
不过大多数时候,这个小世界其实不专属于我们。
有一位神奇的疯老头也在这里,就住在这满天星河当中。
每当我在知了叫声的掩护之下溜到这里时,他总是斜躺在工厂主楼废掉的台阶上。天为被,地为床地就这么睡着。
时不时醒过来,看见躺在离他不远处呆呆地望着漫天繁星的我,就对我投以一个令人安心的笑容。
我总是来不及回应,便看着他再一次沉沉睡去。
这位神奇的疯老头之疯,在于镇上人们说他精神有问题,明明有手有脚,却什么正经活都不愿意干,搞得到头来老婆也跑了孩子也跟着走了;明明还剩下一间不大的房子,却永远只在东北最严寒的那几个月才住进去,平时有家不回,非要自己一个人躺在那个废工厂里。
这位神奇的疯老头之神奇,在于他有时没睡着,会给我讲一些神奇的故事。
他喜欢讲童话,比如他最喜欢讲的,就是曾经有一个国家:那里的人们无需担心任何事,小时候,会有一些你甚至不认识的人给你饭吃,教你识字;等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就会有学校自动让你去上学;等你上完了学,工作岗位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你的面前;等工作一段时间后,一间房子就会从天而降,让你舒适的在里面生活;如果生病了,可以去一间好大好大的屋子,里边穿白衣服的叔叔阿姨们会免费帮你治病,前提你是个不怕打针的乖孩子。
他说,在那个国家里,钱似乎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大家仿佛一个大的班集体,如果有谁表现好,就会奖励他几分,等攒够了分数,他们就可以用这些分来换取一些额外的东西,大多数时间会是一台收音机,然后这位换到收音机的人就会真的像刚刚拿到新玩具的小朋友那样,高兴地呼唤大家一起来玩。
他说在那个国家里,即使最富有的人也不会比最穷的人富有多少;即使地位最高的人也不会瞧不起地位最低下的人;即使最有权力的人也不会滥用他的权力去满足一己私欲。
他还说,在那个国家里,只要你劳动,那不论你是干什么的,你都会赢得夸奖与赞美。
那个国家虽不富有,但大家都很快乐的生活着。
我问他:“这个故事也是很久以前的吗?”
他叹一口气。
“不是。”
镇上的人也讲故事。
很巧,大多讲的故事都关于他。
他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正值朝鲜战争爆发。他爸爸也与太公一样,热血青年脑袋一热,回过头来才发现自己已经过了鸭绿江,回不了头了。
不一样的是,太公命大,捡了半条命回来。
而他的父亲没那么幸运,牺牲在了那边。
按现在的常理来讲,他的生活中一定是要缺点什么的。可怪就怪在他什么也不缺,活得还挺快活。
更怪的是,那个年代的这种人,好像都是这样。
他没有父亲,于是合作社的社长带头组织乡亲们成立了一个小组,每个男同志轮流为他家干一周的农活。并且在此期间要代行他父亲的职责,当然了,谁也不准代行丈夫的职责!
社员听完哈哈大笑,说那这忙我们不帮了,然后第二天还是乐呵呵的过来填了排班表。
因为不是亲生父亲不好下手,异于那个时代的是,这孩子小时候居然没怎么挨过打。也因此,从小他的名号在全镇就是出了名的响,力气那是出了名的壮,脾气也是出了名的淘。
哪天要是谁家房子上的瓦片又少了几片,那十有八九是他又翻上去了。
这可真是伤透了做母亲的脑筋,这熊孩子该怎么办才好呢?
唉,愣是没个辙。
时光仿佛田野里与大人们捉迷藏的孩子,就这么一年年地溜过去。不声不响,谁都知道她在那,却又谁都抓不住。
后来,合作社改成了人民公社,规模也是大了不少。那天县里来了人,叫大家伙聚到一起,然后拿个大喇叭跟同志们嚷嚷,说最高指示:要让知识成为人民群众手中最有力的武器。于是帮忙在公社里加了一间图书室,还找了个人来帮忙教书认字学加减法。
于是过了一段时间,正当母亲找不到孩子,又以为孩子去哪撒野了,人家突然找过来,问你家孩子这么厉害的吗?母亲一听楞了,说那犊子又干什么呢,怎么了这是?人家接过话来,笑着跟母亲说,赶快去公社里图书室看看吧!你儿子在那捧着本书看呐!
她一听也乐了,我家孩子要识字了!将来肯定大出息!
在图书室里,她问他,说,你都看些什么呀?
他指指一本巨厚无比的机械工程学书籍里一张大机器的照片,说,看这个,这个长得帅!
旁边一直没说话的图书管理员兼本镇目前最高文化水平的人兼这一片地区的扫盲运动的负责人笑了两下,插了嘴,说小朋友你知道这东西能动吗?
小家伙俩眼冒光,什么?这么厉害的东西居然还能动?
哈哈!这东西就是因为能动才厉害的!
孩子眼神都直了,只顾着一个劲的“哇——”,连哈喇子淌下来了都不知道。
“那小朋友啊,”他看着眼前这个眼中的光芒仿佛嘴里的哈喇子一般晶莹剔透的小孩说道——
你想不想学怎么能让这个厉害的东西动起来啊?
自那以后,他还是镇上最调皮捣蛋的,但也成了为数不多知道机械工程技术的孩子。
再后来,大概60年代末吧,镇上要盖一座巨大的工厂,邻里各镇都来了人。大家说,这下咱们镇可就发达了。
拜之前的扫盲班与之后的几位知青所赐,现在大家都知道,这叫投资第二产业带动当地经济,推动地区城市化。简而言之,就是这个镇,就要开始往北京那样的大城市齐步走了!
大家高兴啊,说这下我们镇可真真算是威名远扬了一回,虽然这威名其实连市都没扬出去,但那群质朴的脸上还是透出了令人羡慕的笑容。
后来有人研究,说这种笑容叫满足,又称作幸福。
这种笑,在现代人的脸上是很难找到的。
他当时折腾的一身腱子肉,年轻力壮。正好被来施工的大队看见了,说小伙子我看你身子骨硬朗,帮帮忙,你骑着这辆三轮车,去县里运70公斤水泥过来吧,再帮我们干干活。
那会,进工地干活可不像现在。那会干这个的可一点都不可耻,劳动嘛!谁敢说劳动人民一个不字?
他二话没说,蹬着三轮车就往县城去。
“回来!回来!走反了!路在左边!不是右边!右边到不了!”
他这才扳过车头,然后火急火燎地往县城赶去。
再往后,厂子投产了,他作为又有力气也有知识的那一批人,率先地进了厂。
人们都夸他干的真好,次次表彰大会上老是有他的名字。那会没有现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妒忌,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上他家里,赞不绝口地把他的奖状摸了个遍,然后挨个向他学习工作经验。
有一天,他发现这一两个月居然不知不觉就得了这么多工分,而且还没怎么花,于是就考虑干票大的。
几天后,一台崭新的半导体收音机,出现在了厂里。
大家都围着这个新鲜玩意打转,他也不像现在的人那样得到了什么就马上要藏起来。大家开开心心地围在一起,听着东方红一号晃悠悠地就上了天,然后收音机里面就晃悠悠地“东方红,太阳升”起来。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嘿呦,他是人民大救星......”
大家也都跟着唱。
唯独她唱的与众不同。
宛如百灵鸟从森林中飞起一般,她天神一般的声音穿过一片歌声的森林,直直地飞进他的耳朵里。
抬头一看,妈呀,敢情七仙女回天界的时候,在凡间落下一个?
绿色的军服穿在她的身上,居然变得比最名贵的晚礼服也要美丽上千倍百倍。两条麻花辫子一甩一甩,一下下全落在他的心上。仿佛是有人想要把世界上所有美好的词汇具象化,这才造出了她。
终于,在一段土的掉渣还极其富有时代特色的情话之后,二人就这么定了终生。
又一段时间之后,二人站在“批斗大会”上,老老实实地向各位革命群众如实回答了二人的恋爱经过,就这样,一场极具时代特色的婚礼过后,二人领到了结婚证,和一把房门钥匙。
镇上人讲到这里,无不捂住脑门,大叹好好一个人,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个鬼样子。
我看着他,他看着我。
我又看看后面荒凉的工厂。
我指指工厂,又指指他。
“怎么搞的?”
怎么搞的?童话不是到这里就该结束了吗?
他看看我,然后无奈的笑笑。
仿佛世界上最后一个人面对着即将毁灭的地球,万念俱灰地笑了几下。
“唉......怎么搞的呢......”
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
麻花辫变成了大波浪,呢子衣代替了绿军装。
身后密密麻麻的堆着曾经的先进工作者奖状,却换不来她与孩子的笑脸一张。
他解释过,工厂就算停工,就算是把他们这群工人全都赶出去,他会俄语,懂机械,文化水平很高,他不会找不到新的工作的。
“但你赚不到钱。”
她这么回答。
“工人明明是最光荣的职业,明明是最该赚钱的,以前我们不是赚的很多吗......”
他愣住了。
是啊,以前。
今时不同往日。
与门外那个靠卖假药倒国企货发家的金链胖子比起来,无论他有多少学识,不过臭工人一个。
她告诉他,即使工厂不停工,孩子和我也必须走。我们不能在这么一个破地方浪费一辈子。
他再也不说任何话了。
他输的彻彻底底。
他们输的彻彻底底。
这叫现代社会,现代社会讲究金钱至上,现代社会才不管你那些什么狗屁理想。在现代社会,别管你多厉害,赚不着钱?那就去你妈的!
他就这么走出家门,身后是他死掉了的小世界。
他也不知道要去哪。
去哪啊?
他走着走着,晃到了一个路口。
哦。他记得,这是好久以前,刚刚盖工厂那会,他骑三轮车去县里拉水泥的地方。
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路过。
“喂!回来!回来!走反了!路在左边!不是右边!右边是死路!走不了!”
没有人理会他。
他笑笑,当然了,怎么会有人理会他呢。
后来,荒废的工厂又有了生机。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世界不会让一个地方空白太久。
人走了,自然就要重新占领这里。
不过倒是有间屋子一直住着人,与外面杂草丛生的世界相比,这里虽然简陋,但干净整洁,俨然一副《陋室铭》景象。
他不想走。
我又抬头看看工厂:“所以就这样了?”
“所以就这样了。”
春去秋来,我再一次回到小镇。
工厂已在半年前被彻底拆除。
......
葬礼上人很少。
太公说,那个童话故事,他也知道。
曾经大家都知道。
他的坟冢高高地立了起来,碑前放着太公帮忙点着的三支香。
那青烟就这么冒着,越冒越高,直到飘入云中,逐渐不见踪影。
仿佛直直地通往那个童话中的乌托邦一样。
都说,人死后是要去一个地方的。
也不知道他回到那个乌托邦了没有。